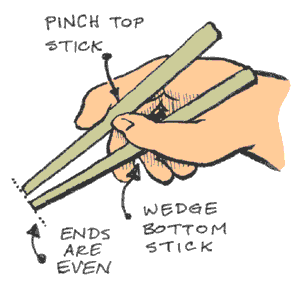秋去冬来。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排练,我们的“山寨戏”得登台啦。最后的准备工作是服装;《海港》编的是六十年代的故事,便装就可以当戏装。只有马洪亮马老头的衣服费点事儿,是中式大褂;不过这也不难,港务局的工宣队脱一件就有了,呵呵。
第一次“公演”是在港务局的大礼堂。那时镇江是长江上的重要港口,客运、货运有九个码头;港务局的办公区也很大。礼堂的舞台演戏没问题,还有后台可以化妆、换衣服。
舞台化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假如你脸上啥也不抹就往台上一站,被灯光一打,那准是煞煞白,面无人色。而且从台下看上去,人物的眼睛鼻子就像是雾里看花似的。所以戏剧妆都是很浓很夸张的:眼睛描得又大又黑,嘴唇抹得又鲜又亮,几十米外大概也不会认错呢。假如是古装京剧,那还有特别的妆,画成花脸、小丑、花旦什么的。幸好《海港》是现代戏,所以用的是话剧妆。
虽说话剧妆简单些,也有好几道工序:先打底妆,变成一张粉红的脸;再涂腮红,两颊就有了血色;闭上眼,用粉扑沾了定妆粉扑得满脸,再用软软的大毛刷把多余的粉掸掉。接下去就是精细活了:用眉笔描眉画眼,用口红勾出唇线,再涂满嘴唇;马洪亮得加几道皱纹,点一脸胡茬子。钱守维得画得丑些,眉毛向下,凸显“阶级敌人”的阴险…
用的都是粘粘的油彩,从牙膏一样的管子里挤到左手的手背上;那手背就是调色板,根据各人的肤色和角色,调成不同的底彩。再用手掌上妆,有时左右开弓,好像在打耳光。几个主要人物,都是董老师、李老师给化妆;其他的演员,大家先自己打底妆,再排了队,让别人像流水线似的给定妆、画眼、点唇。咱这打板鼓的不上台,也没闲着;替别人化妆,自己也沾了一身的粉墨油彩,还觉得挺好玩。
化妆、穿戏服就得花上俩小时。方老师和顾老师指挥大家把布景道具放好,乐队坐进舞台右侧的“乐池”,一切就绪。大幕拉开,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,不但座无虚席,连靠墙也站满了看戏的。
张同学剪了一头短发,画上妆,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,英姿焕发,还真有几分正宗方海珍的模样,一出场就博得满堂彩。马洪亮的一段“大吊车,真厉害,成吨的钢铁——,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,哈哈哈哈!”就更是受欢迎了;要知道,台下坐的是成天在码头上干活的人哪!
戏就这样一场一场地演下去,没失误,也没笑场,连个咯噔都没打。咱的板鼓虽然敲得不专业,好歹滥竽充数蒙混过去,没出乱子。最过硬的当然是张同学的金嗓子,高音低音,散板快板,一点都不含糊,在业余演员里是很出类拔萃的了。
一戏终了,观众鼓掌,演员谢幕。大家涌进后台,叽叽喳喳,都很兴奋。老师们也松了口气,几个月的辛苦,总算有了结果。接下去是卸妆;把凡士林一团团抹到脸上,再拿细草纸擦去油彩。都收拾完了,食堂给我们准备了夜餐,每人一碗面条;这时离我们的上一顿饭已经六、七个小时了。
这台戏在我们那儿演了有十几场吧,记不清准确的数了。那时娱乐太少,“山寨戏”也很热门呢。提起一中来,大家都知道我们排了一出连台大戏,“方海珍”演得很棒。张同学不久就当了兵,听说是被部队文工团招去了。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?还记不记得这段轶事?
几个月后,我初中毕业了。那是文革开始后第一届没有下放的毕业生,我的同学们大都进了工厂当学徒,像《海港》里的韩小强一样成为体力劳动者。我因为随母亲下放,户口在农村,不能分配工作。幸好高中恢复招生,我得以继续念书
——“塞翁失马,安知祸福”啊!
上高中以后,董老师继续教我音乐。我组织学校的文艺活动,像每周一次的广播教唱啦,每学期一次的文艺汇演啦,一直都有董老师指导。几年前回家乡,陪另一位老师去参加退休教师的文艺汇演,意外地见到了董老师。她两鬓有了白发,却还是那样热心,从台前忙到台后。
顾老师也教我的高中美术。她曾经有心培养我正经学画,让我去参加课后的绘画小组;可我那时给学校的黑板报当总编,从约稿到抄写,忙得实在没时间学画,忍痛放弃了。不过回过头来想,我并没有绘画方面的特别天赋,放弃还是对的。因为这,对摄影却有了兴趣,好歹可以弥补一些不能画画的遗憾吧?
高中最后一学期,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。他上课和导演戏剧一样,也是声情并茂,不负“李激动”的名声。那年,毛泽东在搞“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”,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风云人物;我们这些高中生也跟着反对考试,包括我自己,尽管我并不怕考试。那个学期,李老师只讲了两个内容:一首辛弃疾的【菩萨蛮】: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…”; 剩下的时间,就全用来讲《红楼梦》了。那年头《红楼梦》是上层也喜欢的,不是禁书,但也不是教材。李老师是想教点真正的文学作品,同时又不至于给他自己带来麻烦,用心良苦啊!
期末考试,李老师让我们任选一题:或者在课堂上朗诵那首【菩萨蛮】,或者写一篇关于《红楼梦》的作文。想偷懒的可以偷懒,想表现的可以表现,可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多数人选择了朗诵,我选择了写作文,评关于探春接手管理大观园的那一段。
(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