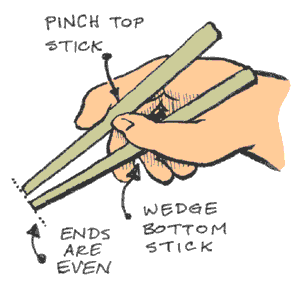排戏、制作布景的同时,乐队也开始成形。“文场”,有京胡、二胡、高胡、扬琴、月琴和唢呐;“武场”,有大锣、小锣、钹、铙;虽然阵仗不大,也算齐全,独独缺一个敲板鼓的人。
京剧的板鼓,其实是乐队的指挥。这个人必须详熟全剧,包括乐谱和锣鼓谱;可那会儿,初中生里懂乐谱的非常之少,而且懂谱的人多半也拉乐器,已经被董老师征入乐队了。看我在那儿“无事忙”,这“鼓佬”的差事,就阴错阳差地派给了我。
虽然初二的时候,我曾经被董老师训练过,给三百人的大合唱打拍子,可从来没有敲过板鼓。按说女孩子打板鼓,多少有点不入流;不过我是那种喜欢尝新的脾气,觉得没啥好怕的,学呗!
《海港》的全剧简谱一出版,乐队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了。老师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副板鼓,咱就开始学当鼓佬。那板鼓就像这图里的,敲起来清脆嘎嘣。
拉京胡的朱老师是教数学的,戴一副深度眼镜,说话是上海一带地方的口音,脾气特好。他练琴的时候,常常闭起眼睛,随着琴弓的一拉一推晃着脑袋,很陶醉的样子。和他搭档的是一个姓佘的高中男生,拉二胡,非常安静,专心拉琴,不太说话,连笑脸也难得有一个;他俩配合默契,把主要唱腔一段段地练过来。我就跟着他们“敲边鼓”。
刚开始,我的板鼓是四平八稳,隔一拍敲一下。练了一阵,朱老师说,“你这么敲太单调了,得敲点花样出来;有的地方敲,有的地方不敲。”可是乐谱上并没有标明,听戏也不是很清楚。再请教朱老师,他说你去找京剧团的学吧。
董老师还真是有办法,找到了一个“京剧团的”。和我同年级有一个姓钱的女生,她爸是京剧团的演员,答应去找京剧团的司鼓,给我上堂课。
小钱和我个子一般高,有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,一笑就弯弯地眯起来,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。她爸是演“刁德一”的,给我讲过她爸“救场”的故事,把我给笑翻了:在《沙家浜》里演胡传魁的花脸,也在《红灯记》里演鸠山。有天演“智斗”一场,胡传魁不知怎么犯了糊涂串了戏,该对阿庆嫂说“我问你这新-四-军-”,却脱口说成了“我问你这密-电-码!”台上的阿庆嫂愣了,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茬;胡传魁呢,压根没意识到他说错了台词,转不过弯来。眼看着就要冷场,刁德一急中生智,对胡传魁说:“司令,咱先别问她密电码,咱先问她这新-四-军!”那边厢阿庆嫂会意,立刻接上:“新四军?有啊,有啊——” 俗话说,“救场如救火”;虽说刁德一是反派,可在台上救场的人,都是英雄呢!
小钱家在京剧团宿舍,和那职业的“司鼓”住一个院;人家一看我那样,就知道完全是个“鼓盲”。所以也不用给咱教啥深层的了,就扫盲吧。他告诉我敲板鼓是手腕的活,别老是大臂小臂一起挥;伴奏的时候,鼓点可以随意;又教了我一些常用的锣鼓谱
—— 就这已经够我练的啦!
咱这一开练,也是够着迷的。在家,拿筷子练;在课堂上,拿手指练;练得手腕酸痛,满脑子尽是锣鼓点,一开口就是“大大大大台!”
这锣鼓点,也是有谱的,但记法并不规范;有的用符号,有的用字。比如这个常用的鼓点吧:
“大八 大八|乙八 乙|仓 仓|台七 台|仓(亮相)|”
“大”、“八”是板鼓,“台”是小锣,“仓”是大锣,“七”是钹。“乙”也很重要,是休止符;假如没有“乙”,就读不顺口记不住了。
练多了,咱也开始欣赏京剧的锣鼓。那节奏,和唱腔的一板一眼、动作的一招一式协调,真是没话说。你能想象人物的“亮相”没有那么一声提神壮气的“仓”吗?少了那由慢及快的“嘟…”,长长的拖腔又会失去多少戏剧性!
这一段当“鼓佬”的经历,培养了我对京剧音乐的喜爱。直到如今,听到板鼓的一声“嘟儿”,咱的耳朵就立马竖起来,像当兵的听到“立正”一样,哈哈!
(待续)
附:京剧锣鼓字谱说明
仓 大锣、钹、小锣
才、七 钹、小锣
朴 钹闷奏
台 小锣强奏
另 小锣弱奏
大、打 板鼓右手强奏
八 板鼓左手或双手强奏
龙 板鼓弱奏
冬 板鼓击鼓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