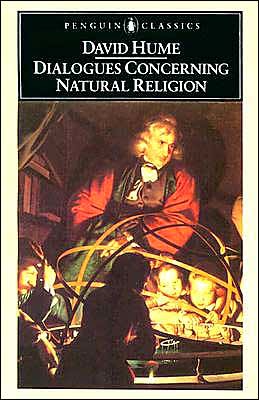苏格兰爱丁堡的休谟塑像
大卫.休谟(David Hume,1711年–1776年)是苏格兰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和历史学家,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本节主要介绍他对“自然宗教”的怀疑。
18世纪的“自然宗教”认为,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了解可以认识上帝;自然界是仁慈的、完美的、全能的,由此引申出造物主的仁慈、完美和全能;上帝设计了人的天性,使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分辨善与恶,形成道德观。休谟认为自然宗教过于乐观,自然界非善非恶,研究自然界也不能将人类引向上帝、引向道德。
今天看来,休谟说得很有道理。几百年来的历史证明:自然科学可以用来做好事,也可以用来做坏事;认识了自然界可以让人成为天使或者恶魔。道德的约束,大概还要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地方去寻找。在休谟时代的欧洲,是从基督教中找;在今天的中国,从哪里找?你懂的,呵呵!
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【现代思维的诞生】的译述,不代表我的观点。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,鸣谢!
——风铃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前面讲过牛顿在文化上引起的惊人反响、新哲学产生的自然神论、持乐观主义的自然宗教、以及乔瑟夫·巴特勒主教的“天然人性”理论。这个脉络显示出18世纪乐观的自然宗教的两大基石,1.相信人类具有上帝赋予的感官和思维能力,让我们通过了解大自然去认知上帝;大自然是人类通向上帝的中介。2.上帝设计了自然界和人类的互动,从而让人类受益。二者都是从17世纪的思想革命继承下来的,是席卷18世纪的潮流,它们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的欧洲文化。
但是也有“反潮流”的思想家,对那种乐观的“自然宗教”表示怀疑。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:休谟和伏尔泰。这节先说休谟。
休谟《自然宗教对话录》
休谟在这方面最深刻、最有针对性的著作是《自然宗教对话录》(Dialogues
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,1779)。这本书休谟在世时没有付梓出版,但他的朋友们都读过。朋友们对他说:你这本书太危险了,先别发表。这些朋友大多是神学学者。从理论上来说,休谟在书中并没有说自己赞成哪一种观点,他只是把对于自然神学的不同看法写出来,借一个名叫费罗(Philo)的人物之口,对“新哲学”进行了分析和评论。休谟的朋友们很担心他在身后会遭到不利的评判,建议他把书中费罗的观点冲淡一些;休谟考虑了很久,加写了最后一章,使他的观点看上去比较“安全”。但贯穿全书的,仍是费罗对于自然宗教的基础所表示的怀疑和挑战。
自然宗教的基础是:人类具有上帝给予的感官和理性,能用归纳法、演绎法从自然现象的数据中找出宇宙的规律;从自然界的有序和仁慈中,我们能推断宇宙是由智慧的创世者所设计的,那智慧的创世者就是上帝。上帝是仁慈的、全能全智的。这个理论把宗教建立在对于人类经验的归纳上。
费罗指出了自然宗教的四个致命缺陷:
1.
这个理论把宗教变成了不确定的东西,因为人的经验并不能保证一定是真知,而只是接近真知的过程。这就好像在说:“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上帝,但还要看明天我从自然界会学到什么。”作为宗教,这种不确定性不能令人满意。
2.
把“设计一座建筑或一台机器”比作“创立宇宙”,这种类比不足以说明问题,因为二者之间的相似是很有限的。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类似之处。在科学归纳中,这种差异很重要,不能忽略。树木浆汁在树体内的流动和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有一点类似,但又有本质上的不同;傻瓜才会用树浆流动的道理来解释血液的循环。假如某人解剖动物,说“啊,这就是血液循环系统。”这对他所解剖的动物而言是正确的;假如说树浆也有同样的循环系统,那么树首先得有心脏啊。
3.
我们只观察到一个宇宙,不能类比。假如我们观察了多个宇宙,那么从一个宇宙的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可以放到另一个宇宙中去验证。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不但只有一个宇宙,我们对它的了解也是微乎其微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说,我们如何能够去归纳宇宙的因果关系呢?更别说验证结果了。
请注意:这里说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,而是如何认知上帝的问题。我们通过什么知道上帝的存在?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知道的吗?
4.
在科学上,如果要确认某一个假设的正确,就不能有反例。一个反例就能推翻假设。如果你认为房屋附近的植物长得好,只让我看那房子附近有一两棵植物确实长得好,但却不看那些虽然种在房子附近、却长得不好的植物,或是离房子很远却长得很好的植物,那你就是带有偏见、倾向性,就是不客观。选择性地採证是反科学的。(我们周围有多少选择性採证的例子!大家各取所需,包括有些所谓的专家。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就是一例。——风铃) 休谟笔下的费罗说:当人们讲“这个宇宙是智慧、全能、仁慈的,因此宇宙的设计者也一定是智慧、全能、仁慈的,”他们只用了正面的证据,而忽略了负面的证据即反例。他们举例说明宇宙是有序的:“看看这不平凡的天吧,我们需要雨水,结果就下雨了,植物就生长了,大自然多么仁慈!”但他们怎么不说天也有旱灾、也有洪水呢?怎么不说那些让人类辛辛苦苦建造的东西毁于一旦的暴风雨呢?怎么不说星球的相撞呢?怎么不说天灾呢?仅仅例举“有序”是不够的,因为还有很多“无序”的证据,同样需要得到解释。如果说宇宙是“智慧、全能、仁慈”的,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天灾?事实上,这些正反两面的证据让我们相信:宇宙有时候有序,有时候混乱无序;有时候对人类有利,有时候对人类不利。用它来类比上帝是正确的吗?
休谟更进一步地指出,即使允许自然神学做这样的类比,把宇宙的设计和建筑设计相提并论,用人类的智慧去想象造物主的智慧,也还是不能从宇宙推断出自然宗教的上帝。自然界是有限的,但上帝却是无限的。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有缺陷,可上帝却是完美的,怎么能有缺陷呢?宇宙倒更像是一个顽皮的神造出来的次品,被上帝扔掉,被我们捡着了。所以不能通过研究自然界去认识上帝。
休谟说,也不能从人类造物的经验去推论上帝的创世。想一想,人建造一艘军舰尚且需要很多个人的合作,需要很多双手。宇宙更大、更多样,我们只能推论出宇宙的创建需要很多的“手”。我们人类的经验太狭窄、太有限了,不能据此理解上帝是怎么创世的,没法推论出上帝独立的能力和超自然智慧。
人类一直在改进自然。医药不就是对于自然的改进吗?对于小孩和老人的照料不是对自然的改进吗?农业不是改进自然吗?给牲畜配种不也是改进自然吗?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即使在自然界,变化也是经常发生的,时好时坏。这样时好时坏的机器,像是一个完美的造物主的作品吗?从这样的自然界,能推测出上帝的完美吗?
再看邪恶的存在。休谟通过费罗说:如果自然界具有上帝的无限仁慈,那么看一看人类的历史记录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悲惨、痛苦、不确定的生活?假如仁慈且智慧的父母能够把子女从疾病、地震、痛苦的死亡中拯救出来,他们定会拯救;若他们救不了孩子,那我们就不会称他们智慧、仁慈。假如自然界是仁慈智慧的,那么它就不会让我们人类遭灾。自然宗教认为“物种的生存”表明了造物主的仁慈,但物种的生存却是它们互相残杀的结果。只要去医院的儿童病房探访一下,就会觉得这世界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是由完美、仁爱、全能的神创造的。看到孩子们受的痛苦,你会说“这正是我所预言的无限仁慈、智慧、全能的神所造的”吗?
休谟的结论是:自然界不是尽善尽美的,因为存在着痛苦和缺陷。它也不全是邪恶的,因为存在着健康和快乐;自然界更不是善与恶的永久争战,因为存在着普遍的自然规律。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有一种:自然界既不仁慈也不邪恶。
通过费罗之口,休谟表达了他的观点:人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,但研究自然界并不是认识上帝的途径,也不应该把“天然的人性”作为道德的指引。以为人类用自己的感官和理性了解自然界就能认识上帝、得到道德上的指引,那是太乐观了。(这一点已经、正在、将要继续得到证实。如果没有制度的、道德的约束,人性之恶就会泛滥。——风铃)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(艾伦.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《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》的总编辑。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,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《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: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
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》。更多资料见:http://www.thegreatcourses.com/tgc/courses/course_detail.aspx?cid=447)